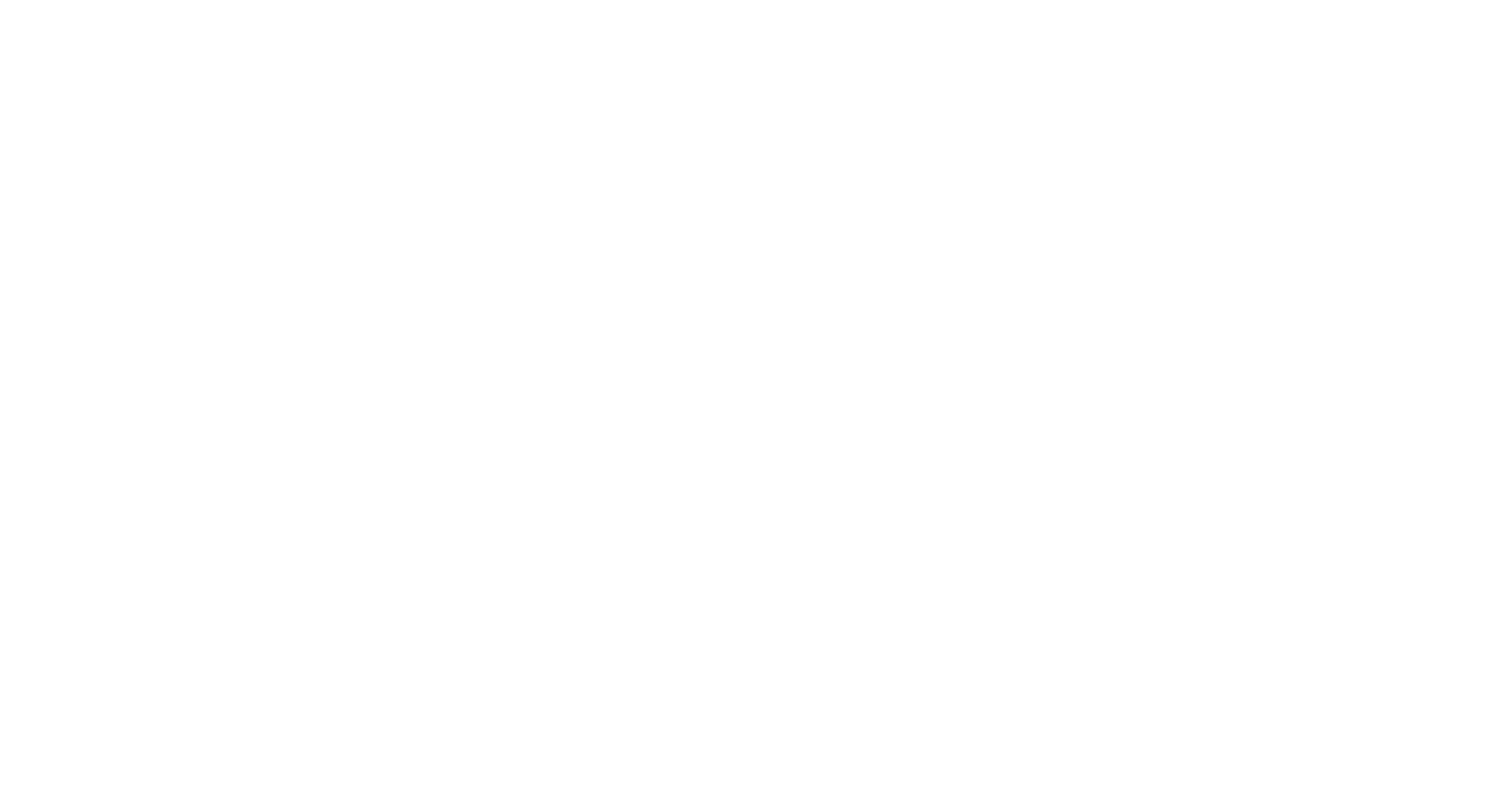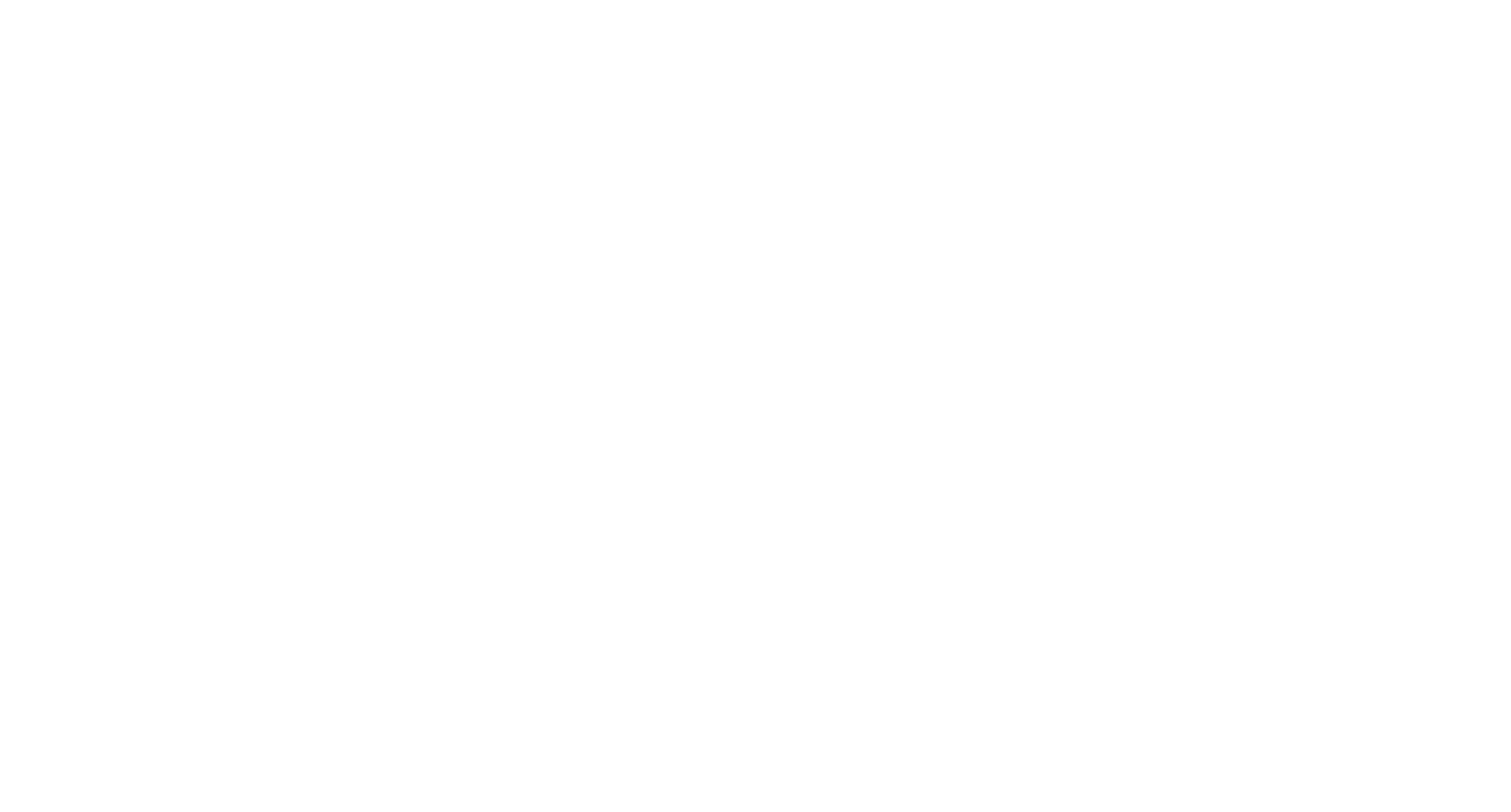超对象:陌生访客
展览现场
精选作品
前言
在《生态思想》中,我创造了一个术语“超对象”来表示相对于人类来说在时间和空间上大规模分布的事物。
——蒂莫西·莫顿
艺术是关于感知的,而感知则需要一个对象。我们经常谈论艺术经验的陌生化,“超对象”就是这样的对象之一:它们在时空中存在的规模过于庞大,同时又是我们日常生活、谈话的基础,以至于很少有人(能)将它们作为一种 “对象”来感知。比如,弥散在空气中的电磁力场,若失去它们,气候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,而手机通讯也无法正常工作。或者每天通过皮肤与人体交换数十万次的细菌和微生物,它们不仅携带着生命起源的代码,更是共同参与、定义、影响着“人”的行为。在过去的艺术中,它们从来都是被遮蔽的;而现在,在后人类、生态艺术的麾下,它们涌现般的展示着自己的“在场”。
参展的三位艺术家在各自的领域中深耕、思索,既相互独立,又彼此交集。他们所处理的艺术对象都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现象学,在一种更广袤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着实践。这些对象在“实在界”中如幽灵般徘徊,唯有通过艺术家之手,才被截图和捕获,进入我们言说和感知的范围。
狄思奇:欲望的制图学
狄思奇的绘画“Geogory 1”是一片未知的地貌,它无限地延展开去,没有任何标志性的凸起——也就是说,它等待着被开发和殖民,等待着被命名。我们常常忘记,“命名”才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开端,欲望在身体的孔洞中流淌,向外部空间发出声音来标注和定位自身的存在:未被命名和言说的世界就不存在。在“新世界地图”系列中,他依靠语音的流动创造了一幅幅假冒的地图,声音像液体一样扩张,如膜一般产生着张力,支撑着一个个虚假的图景。地图,从来都不仅仅是关于知识的,而是“欲望的制图学”:声音是通过获得权力而忘却恐惧的。
孙澜赫:“兽-人”
孙澜赫用一种萨满式的眼光,从现代人的躯体中召唤出动物性,创造出“兽-人”这一新的生命界面。显然,这条路径来源于乔吉奥·阿甘本和唐娜·哈拉维关于动物与人关系的论述,但是,在孙澜赫这里,“神圣动物”不是末世的救赎,后人类的历史也并非无差别的协议。在他的“东北-伦敦-深圳”的跹跃中,在他对体育史和殖民史的研究中,他发展出两个并行的角色和场域:"人-兽"(竞技场)和"兽-人"(养殖场)。“全球历史"的残酷性在于:这根本不是地方经验这样虚伪的问题,而是"人一兽"对"兽一人"展开的一场野蛮围捕。
徐子奕:器官学的历史
徐子奕在地层中发掘深埋于历史尘埃中的事实,展览中的作品由(已灭绝的)动物化石和人造工具(斧头、箭镞等)组成,如同一位来自异世界的“无知的”考古者,无视有机体与无机体的分类学,粗暴的根据自己的意志创造出历史。事实上,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,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器官学:内部驱动的基因和遗传特征的变动、以“炼金术”为代表的进化皮肤套装和身体装置。这两类器官的进化都构成了史诗,不过,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中,前者惊心动魄的程度被大大低估了。徐子奕的作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:内在的“生命驱力”意味着什么?以及,是什么让人类如此强大,又如此脆弱?